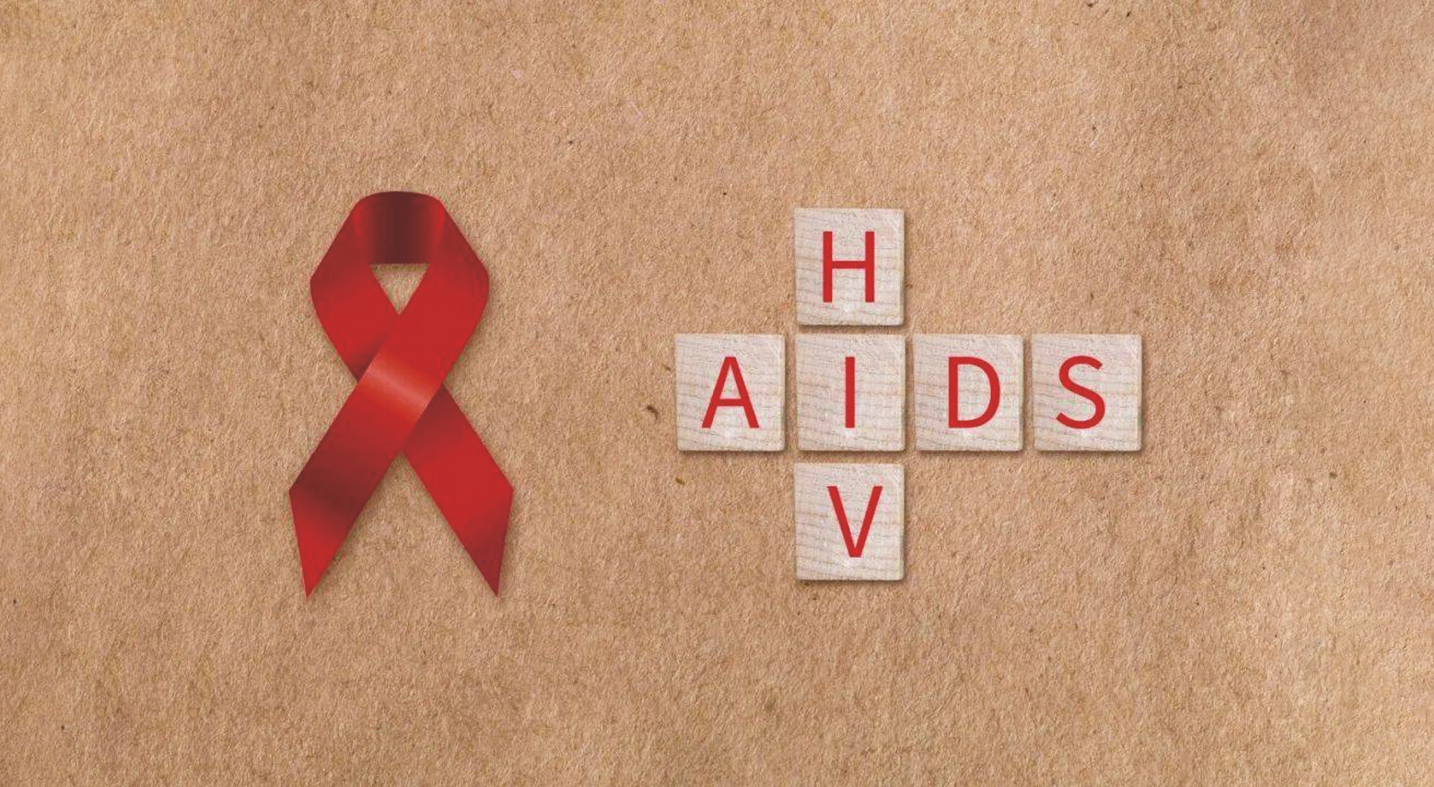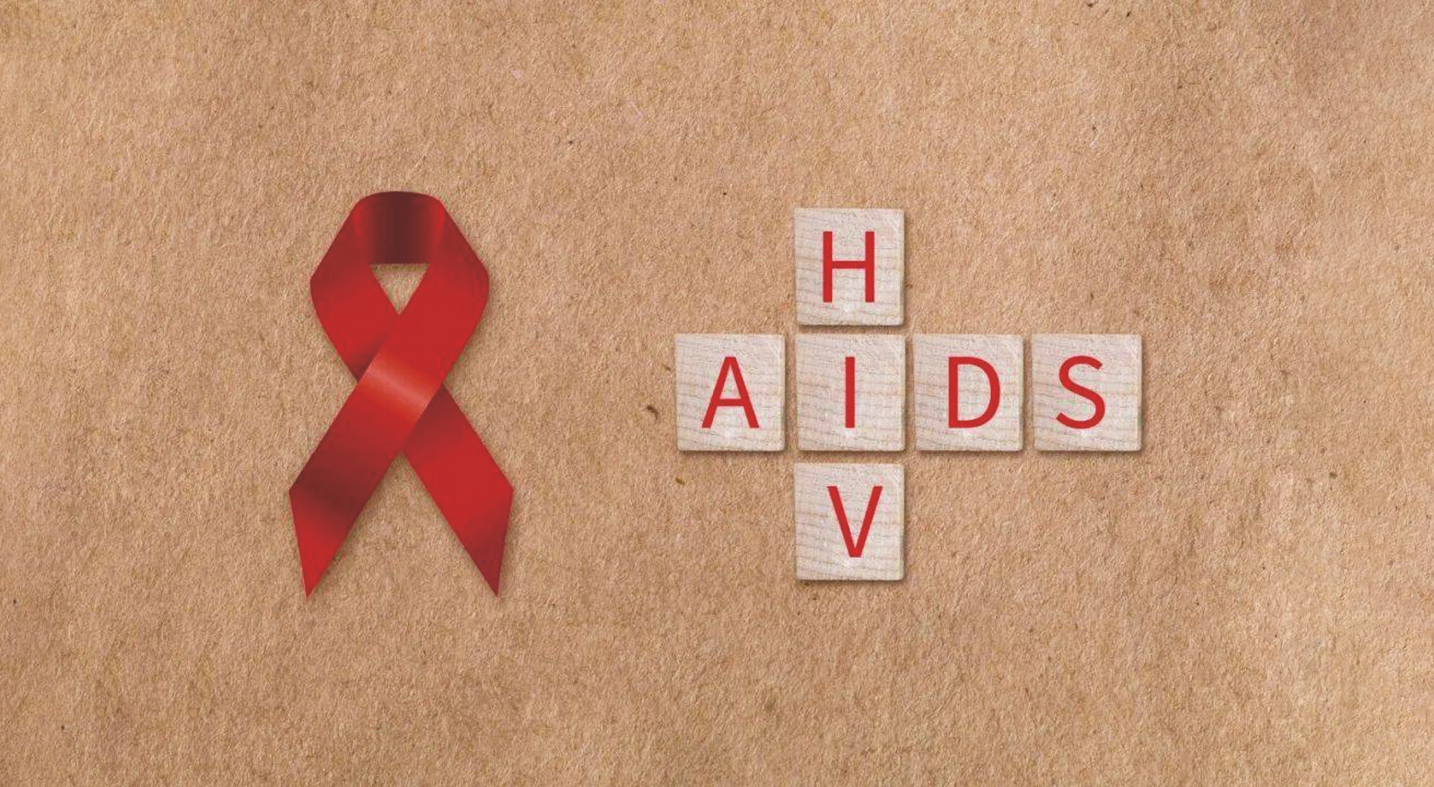
40年前,法国科学家蒙塔尼第一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HIV),然而40年后的今天,治疗艾滋病既无根治性药物,也无预防性疫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艾滋病平均每1分钟就夺走1条生命。
“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最具效益比的科学发明,但艾滋病疫苗研发却是全球公认的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之一。”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教授孙彩军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可自愈的艾滋病患者,已开展的300余项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也都以失败告终。艾滋病疫苗研发为何如此艰难?孙彩军给出了3点原因。
首先,疫苗研发的速度赶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孙彩军表示,HIV基因组具有高度变异性,不同亚型间的变异率高达20%—35%,同一亚型内变异率也可达7%—20%。新冠病毒和流感等病毒的变异率与HIV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协会副主席达格纳·劳弗曾说:“HIV不是一种病毒,而是数百万种不同的病毒,这给疫苗研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其次,对HIV的致病机制研究不够透彻。“与其他病毒不同,HIV只感染人,几乎不感染其他物种。即使偶有感染,也不会引发明显的临床症状,导致研究缺少能够完全模拟人体感染HIV病理反应和疾病进展的动物模型。”孙彩军解释道。
最后,也是HIV最与众不同的一点——目前没有感染后依靠自身免疫力痊愈的艾滋病患者。“即使是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都有患者自愈的案例,但艾滋病迄今没有一例,这导致我们无法获知人体内哪些潜在的免疫指标能够控制或清除病毒,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孙彩军说。
40年间,从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到蛋白亚单位疫苗、病毒载体疫苗、联合疫苗等,艾滋病疫苗研发经历了诱发体液免疫、诱发T细胞免疫应答、同时诱发抗体和细胞免疫三大阶段。遗憾的是,所有临床试验最终均未成功。
孙彩军团队另辟蹊径,通过把单纯疱疹病毒(HSV)改造成疫苗载体,再把HIV抗原克隆进去的方式研发治疗性艾滋病疫苗。“HIV最‘狡猾’的一点就是它能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从而隐藏于细胞内,无法被杀死。但在临床试验中发现的HSV和HIV共感染的特性,能够利用HSV有效激活和唤醒潜伏的HIV,同时让疫苗诱发免疫应答,将病毒载量控制在检测不出的水平。”孙彩军表示。此外,新冠疫情以来,学界认为以mRNA(信使RNA)技术为基础的新冠疫苗的广泛应用给HIV疫苗研发带来了新的曙光。
目前,艾滋病最常见的疗法是鸡尾酒疗法,通过暴露前预防治疗和暴露后阻断治疗大幅降低高危人群感染HIV的风险。
“如果患者严格遵照医嘱,依从性高,可将HIV控制在检测不出的水平,拥有与正常人一样的生命长度。但鸡尾酒疗法需终生定时服药,患者可能产生药物副作用,背负经济压力,还要面对社会歧视等,因此依从性往往并不理想。”孙彩军说。
我国每年都在艾滋病治疗药物上投入了巨额的经济成本,且成本随着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扩大而逐年增长。但孙彩军指出,在全球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依赖高额费用采购维持性药物控制艾滋病的可靠性越来越难以保障。
尽管全球公共卫生投资巨大,但仍有约1/3的HIV感染者未被确诊或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要终结艾滋病流行,还得靠预防性疫苗和根治性药物,这场战役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陈祎琪)